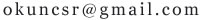陶渊明和李白是其各自时代成就最高的诗人,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都属屈指可数的几位一流大诗人之列,而两人的个性、诗风、人生理想有很大差异,所以历代评论家和学者将陶、李二人加以比较者并不多,但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嗜酒。
李白嗜酒,自不必说,早已家喻户晓。《旧唐书》本传称其“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浪迹江湖,终日沉醉”。李白最著名的诗篇多是酒后而作,杜甫有诗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又说白“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而陶渊明自称“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五柳先生传》)萧统《陶渊明传》言“(颜)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本传记载他任彭泽县令时,“公田悉令种秫稻(酿酒用的粘黄米),妻子固请种秔(即粳米),乃使二倾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今存陶诗一百二十四首(未计联句一首及桃花源诗),据统计,内容有涉于酒者达五十五首,虽没到朱光潜所说“渊明诗篇篇有酒”的地步,也已占到陶诗总数将近一半的分量,而且有许多名作名句都与饮酒有关;陶公还专门写有《饮酒》组诗二十首,为其“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而成,内容丰富,反映了作者许多方面的思想感情,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首更是陶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临死时,陶公还“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其一)。由此可见,饮酒对于陶渊明的人生及文学创作也就如饮酒对于李白一样有着特殊的、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比较的重点放在陶渊明身上,通过分析陶渊明饮酒诗与李白饮酒诗的差异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陶渊明的独特个性。
阅读陶渊明与李白的饮酒诗,可以发现两人的饮酒诗都可分为两个类型、两种情调。饮酒陶诗有的极为消沉苦闷,甚至陷于颓丧,如“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有的恬淡静穆,于平和中显出欣喜之情,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息动,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太白饮酒诗如《将进酒》、《梁园吟》、《襄阳歌》、《行路难》其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月下独酌》其二、三、四等给人的感觉是狂荡不羁、一泻千里、潇洒飘逸,如激流、峭壁、飓风,而《把酒问月》、《山中与幽人对酌》、《自遣》、《月下独酌》其一等作品则平和舒缓或者深沉宁静。就两人各自来说,两种情调的饮酒陶诗并不矛盾,从消沉苦闷到平和欣喜大略能看到渊明精神境界的提升过程,正如朱光潜所说“由冲突达到调和”;而李白的两种饮酒诗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难以想象这两种情调截然不同的作品出于同一人之手。其实不仅是饮酒诗,在全部太白诗中都存在着豪放狂傲与平和冲淡两种类型的作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李白诗歌的壮美和柔美两个方面,柔美即“清真”的风格,反映的是人类的普遍情感,而豪放狂傲的诗作极具个性化,表现了独一无二的李白本色。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比较陶、李二人饮酒诗的差异深入探讨二人个性的不同,从而有助于认识陶渊明的独特个性,所以属于“清真”诗风的太白饮酒诗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我认为,李白的“清真”饮酒诗与第二种情调的饮酒陶诗确实有非常相似之处,但这只是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及太白诗风的丰富性,并不能以此为据否认太白饮酒诗与饮酒陶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故而本文中所说太白饮酒诗是只就其壮美风格而言的。
太白饮酒诗的基本风格是豪放、壮阔、狂傲,充斥着躁动不安的情绪,与作者一贯的艺术风格相一致;陶渊明饮酒则平缓、深沉、宁静,这也是陶诗的主要特点。可见不论陶渊明还是李白的饮酒诗在其各自的创作中都不是游离于主体风格之外的作品,二人的饮酒诗与其其他题材的诗作具有相同的艺术风格,亦是作者人生品格的写照,正如任何人都不会把太白想作渊明或把渊明当作太白一样,我们也决不会将二人的饮酒诗相混淆。李白的饮酒诗具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的雄壮气势,渊明却如“山涧清且浅”(《归园田居》其五)般小巧玲珑。李白酒量极大:“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斗酒十千恣欢谑”(同前)、“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美酒三百杯”(《月下独酌》其四)、“金樽清酒斗十千”(《行路难》其一),数字多以千百计,应是以巨盅狂灌豪饮;而渊明,“忽与一觞酒”(《饮酒》其一)、“一觞虽独进”(同前,其七)、“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一觞聊可挥”(《还旧居》),总是一杯一杯地小酌慢饮。太白心态之焦躁烦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其一),酒劲上涌以致失去理性,说出些不合逻辑的疯癫之语,如“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襄阳歌》)、“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月下独酌》其二),最后头晕脑涨、天旋地转,“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月下独酌》其三),要人“以水頮面”(洗脸)才能“稍解”(《新唐书》本传);而渊明不论是愁是喜饮酒时心态都平静深沉,愁饮他“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且进杯中物”(《责子》),乐饮他“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饮酒》其七)、“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他饮酒却从不醉酒,就算他说自己“既醉之后,辄题数句以自娱”(《饮酒》序)、“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但我想,就算渊明醉也是那种稍觉恍惚、微有酒意的小醉,却从不大醉,他始终神志清醒、思维明晰,在饮酒时进行人生、道德、生与死、短暂与永恒的哲理思考,于酒盅前悟到了许多道理:“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饮酒》其一)、“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同前,其二)、“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同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同前,其五)、“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同前,其七)、“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同前,其八)、“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同前,其九),当嗜酒变为“沉痼”,溺于其中无法自拔时,他反省道:“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荣木》)并发出了“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的慨叹,而且曾尝试戒酒(《止酒》诗)。由此可见,陶渊明是品酒,李白是醉酒,品酒者静、清、缓、沉,醉酒者动、浊、速、躁。清宋咸熙曰:“古之酒人,当以渊明为最,太白次之,若阮籍、刘伶,直是沉湎酣身矣。陶公《饮酒》诗,昭明太子所云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太白犹有胸中郁勃之气,其不如陶公者在此。渊明中行,太白狂者,身份有高下,出言亦如之,言为心声,信哉!”。
李白醉酒,飞荡飘舞、充满活力,屡屡有纵酒行乐之语但无颓废放荡之感,反而显出顽强热烈的生命力;渊明品酒,或消沉绝望、或淡泊欣喜,都显得轻柔软弱,要么被现实的苦难摧垮了:“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要么只有在放弃对生命的眷恋、不再在乎生死的时候才能获得快乐:“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同前,其十四)“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同前,其十五)可见,李白的饮酒始终是昂扬、有力量、乐观的,陶渊明的饮酒却总是低沉、软弱、悲观的,两人的饮酒诗不论艺术风格还是思想情调都是截然相反的。
陶、李二人饮酒都是因为心中痛苦,故而借酒浇愁。李白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高歌取醉欲自慰”(《南陵别儿童入京》)、“古人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同前)、“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同前)、“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月下独酌》其四)的诗句,陶渊明也写过“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还说“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朱光潜说:“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底(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底(的)事。”不过正如二人饮酒的情调迥异,他们愁苦的原因也是截然不同的。
李白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是以政治家自居的,他的人生追求始终都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所以李白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政治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求得政治上的成功。和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家一样,李白的本意并不是要作文学家、以诗歌留名后世,文学对于他来说,是扩大影响、使自己名闻天下的手段和工具,是娱情的爱好,也是排遣苦闷的方法,却不是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好炫耀的李白几乎从不炫耀自己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屡屡自夸的都是自己的政治才干。因此,追求政治功名受挫是李白痛苦的根源,为了化解心中巨大的痛苦,他便纵酒放诞。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载,白在宫廷时,“帝用疏之”,他就“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后来被从宫中“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旧唐书》本传)在酒后狂醉中写下的诗篇里他总是发布这样的言论:“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梁园吟》)、“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月下独酌》其四),还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赞美隐士的生活。其实这些都是气话、反话、假话,他正是因为太看重政治功名、圣贤节操,总也不能忘怀,所以愈得不到就愈悲伤,以致靠诅咒来发泄一下愤懑,说过之后气消了便又振作精神投入到追求政治功名的现实斗争中去了。这种“追求-幻灭-发泄-继续追求”的过程可以说是李白一生的一种循环模式,也是他许多著名诗篇的感情套路,像《襄阳歌》、《梁园吟》、《将进酒》、《月下独酌》其二、三、四、《行路难》其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作品都是这样的。从李白的饮酒诗里可以看到他真实的文学才能和真实的痛苦,但却看不到他真实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因此李白是假喝酒,最后说气话、反话、假话,甚至疯话。他饮酒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买醉、忘忧,借酒浇愁发泄过后,心中的矛盾痛苦暂时得到了化解,又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了,他就将酒杯弃置一旁,不再需要酒了。但是他饮酒后写下的诗篇因其狂荡的气势、恣溢的文采使人们折服,但其饮酒诗和饮酒的行为本身并没有陶渊明那样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寄托。
陶渊明饮酒最初也许与李白一样仅仅是为了浇愁,但渊明痛苦的原因既与李白不同,他对于饮酒的态度又有过两次转变——抑或说是两次精神境界的提升——使渊明从“忧愁饮酒”到“欣喜饮酒”,最后“超越饮酒”。
渊明对于政治的态度与李白正相反,他毫不热衷政治,从来就不想做官。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其八)、“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自诩(《五柳先生传》)。因此渊明从来不是一个政治的人,古人、今人多有搬出晋宋易代几十年间政治大事(如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的擅权,桓玄的谋逆,刘裕的篡位等等)来解释陶诗者,但渊明自己从来没提过这些事,他在当时根本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像李白与上流社会乃至皇帝本人都有密切往来;他认识的官员最高是刺史,最多不过是一面之交,常常往来的不是农民就是西曹、贼曹、主簿、长史这样的州县小吏,高层的政治斗争和陶渊明是毫不相关的,除了那首至今还解不通的《述酒》外在陶诗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关心国家大事。因此,研究陶诗及渊明的为人尽可也应须抛开政治因素。渊明的痛苦,我认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他大概有一种天生的内向性格,多愁善感、优柔寡断,又非常恋家,参与社会生活、奔波行役对他来说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及《杂诗》其九、十、十一中以那么凄苦的笔调抒写了旅途行役之苦,并表达了对于居家生活的强烈眷恋。在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是担任公职、作社会人他就痛苦,而只要能够回到家里过远离社会交往的生活他就快乐。他向往的是“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田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的生活,但或者是因为贫困、或者是为了家族利益,抑或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他“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园田居》其一),“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其一),这种违背心意的生活使他觉得“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杂诗》其三)。其二,性格内向、不喜交际的人往往好沉思,渊明亦然。他常常思考生与死、人生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命运的幸与不幸这种沉重的问题。据我统计,今存陶诗一百二十四首(未计联句一首及桃花源诗)中涉及生与死哲理思考的有四十七首,占三分之一还多,而这个统计是只就字面上直接出现有关生与死的内容为据的,虽没有明确提到但品味诗意可知渊明确实是在思考生死问题的作品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估计比饮酒诗还多,陶诗几乎是篇篇含有生与死的思考。“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其一)、“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其十五)、“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其一)……渊明是不相信灵魂不灭的,他用相当多的诗句反复述说着同一个道理:人一死就归于虚无,任何人也逃不过这可悲又可怕的命运。这使他非常痛苦:“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因为有这两种痛苦,渊明曾经一度沉溺于酒中,“得酒莫苟辞”(《形影神·形赠影》)、“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同前,其四),“酒对于他仿佛是一种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运挑战”,此为陶渊明“忧愁饮酒”的阶段,第一种情调的饮酒陶诗多是此时所作。虽则愁苦的原因不同,但就对于酒的态度来说此阶段的渊明与李白并无两样,无非是把酒当作解愁的工具,在酒中求得精神的麻醉以缓解内心的痛苦,其饮酒的行为并没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寄托。不过因为渊明性格的温和、脆弱,不似激烈的李白狂灌豪饮,写下的饮酒诗汪洋恣溢、气势壮阔,如狂风暴雨,而是小杯慢饮,其饮酒诗深沉宁静、轻柔温蔼,如连绵细雨;也不像坚强乐观的李白尽情发泄了愤懑之后就振作起来,又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而是一味地陷在悲观消沉中,愈饮愈愁,无以自拔。
由于渊明如此饮酒,嗜酒“变成一种沉痼,不但使他‘多谬误’,而且耽误了他的事业,妨害他的病体”,于是渊明进行了自省:“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荣木》)作《止酒》以自警。与此同时,因为他如此悲伤,想到“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其一)、“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其五),而自己又“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园田居》其一),感到非常委屈,产生了一种自怜自爱的感情,于是“及时当勉励”(《杂诗》其一),终于打消了一切顾虑,彻底脱离了现实社会,归隐田园,过自己梦寐以求的隐居耕读的生活,由此获得了良心的平静,也得到了真正的快乐,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归隐之后,渊明的生活内容简单、淳朴又富于情趣,主要是耕作、读书、课子、会友、郊游,而饮酒是贯穿于所有这些生活内容中的一件事。在渊明后半生里,酒融入了他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已经成为渊明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生活中的每一天都离不开酒,不论遇到什么事都会饮酒:悲伤时,他“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三);欣喜时,他“漉我新熟酒”(《归园田居》其五);耕作后,他“壶浆劳近邻”(《癸酉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收获了,他“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搬新家,他“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还旧居,他“一觞聊可挥”(《还旧居》);见幼子顽劣,他“且进杯中物”(《责子》);观孩童可爱,他“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其一);与朋友一起,他“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独自一人时,他“浊酒聊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时,饮酒对于渊明已不仅仅是浇愁的手段,而有了一种永恒的意义。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意就是人生的真谛。而他还说过:“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王瑶释“会”为“理之所在”。我认为此之“会”即彼之“真意”,渊明在隐居田园的生活中体悟到了人生、自然、宇宙的真知大道,所以欢喜地持杯畅饮。此为渊明“欣喜饮酒”的阶段,饮酒是和归隐田园的人生选择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越饮酒就越脱离社会、越坚定了作隐士的决心、越能于田园生活中发现幸福,第二种情调的饮酒陶诗都写于此时。他说“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又说“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同前,其九),饮酒可算是渊明终极精神追求的具象表现,他在归隐田园中、也是在饮酒中感觉到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归宿的欣喜,所以他说:“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
在渊明最富于哲理的作品《形影神》三首中可以看到他由“忧愁饮酒”转入“欣喜饮酒”的过程,《形赠影》是他借酒浇愁、沉溺酒中的写照,因为如此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便有了影对形的批判(《影答形》),这表明渊明已经进入“欣喜饮酒”的阶段,以影所主张之“立善求名”代替形所说之纵酒行乐。这里应注意,渊明心目中之“立善求名”非名教中人所言之“善”、“名”:渊明的“善”是自己良心的安宁,不求彰显于众人,渊明之“名”是建立在自己良心安宁基础上的道德名节,而非他所批判的“但顾世间名”(《饮酒》其三)。渊明归隐田园并不是放弃了善名,而是要在最诚实、最问心无愧的境界上成全它。他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同前,其十),清何焯评曰“恐坠固穷之节也”,可见渊明还是追求善名的,他的隐居、躬耕、固穷都为了做到名实相符、表里如一,他人是可以欺骗的,但自己不可能欺骗自己,所以陶渊明追求的善名和伪君子追求的虚名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因为渊明也求名就把他和名教众人等同起来,否定他作为真隐士的伟大,或因为渊明是真隐士就不承认他也求名。
在“忧愁饮酒”时,渊明处在一种非道德的境界,“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对于人生他采取的完全是不顾一切、及时行乐的颓废态度,到“欣喜饮酒”时,他就转入了完善道德的境界,过自己认为是人生真谛的生活。而在成为道德完人(成圣)之后渊明的精神境界又提高到超越道德的境界(成神),就是《神释》中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境界,如同中国古代哲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亦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人生四种境界之最高者的“天地境界”。这种境界,按庄子的话说就是:“丧我”(《庄子·齐物论》)、“心斋”(《庄子·人间世》)、“坐忘”(《庄子·大宗师》),按孔子的话说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或如佛教所说的“空”、“禅定”、“涅盘”。渊明自己也有诗曰:“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其十四)这就是渊明“超越饮酒”的饮酒,这时他饮的已不是物质的酒本身,而是在忘却自我、与天地相合的超脱境界中显现出的“深味”。我认为,这“深味”是比“真意”、“会”更高层次的人生、自然、宇宙的真知大道:“真意”、“会”是属人的,是崇高的道德,而“深味”是属神的,已超越了人间的道德,与自然万物化为一体。鲁迅说诗人“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但陶渊明正如许多哲学家、宗教家一样达到了这种境界,不过在这样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诗人了,当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时并没有真正地“忘言”,因为还有这两句诗用人的语言写了出来,而在超越人间的道德、臻于化境的境界中渊明真的“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得意忘言”(《庄子·外物》)了。所以渊明在他一生中的三种精神境界下相应地有三种境界的饮酒,但却没有第三种饮酒诗。
朱光潜说:“渊明和许多有癖好(指饮酒)的诗人们(例如阮籍、李白、波斯的奥马康颜之类)的这种态度,在近代人看来是‘逃避’,我们不能拿近代人的观念去责备古人,但是‘逃避’确是事实。”李白饮酒消愁是逃避现实,但他消愁后的结果是继续介入现实,故而他的逃避是暂时的,是假逃避,酒后所说的也都不是真心话;而渊明是真逃避,在饮酒中长久地脱离了现实,不论是哪种境界的饮酒,渊明都是转入内心生活、在个人世界里寻求解脱,他是“酒后吐真言”,不管悟到的是“真意”、“会”还是“深味”,他饮酒诗中所说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陶、李二人的饮酒、饮酒诗正如他们的思想、性格,差异巨大:李白是自信、骄傲、豪放、乐观的,陶渊明是内向、自卑、软弱、悲观的,李白有强大的生命活力而缺少沉思自省的深度,渊明的思考非常深刻沉重,而正因为这种沉重、再加上天性的脆弱,使他“每每多忧虑”(《杂诗》其五)、“气力不及衰”(《还旧居》),总显得病弱无力。
李白嗜酒,自不必说,早已家喻户晓。《旧唐书》本传称其“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浪迹江湖,终日沉醉”。李白最著名的诗篇多是酒后而作,杜甫有诗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又说白“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而陶渊明自称“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五柳先生传》)萧统《陶渊明传》言“(颜)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宋书》本传记载他任彭泽县令时,“公田悉令种秫稻(酿酒用的粘黄米),妻子固请种秔(即粳米),乃使二倾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今存陶诗一百二十四首(未计联句一首及桃花源诗),据统计,内容有涉于酒者达五十五首,虽没到朱光潜所说“渊明诗篇篇有酒”的地步,也已占到陶诗总数将近一半的分量,而且有许多名作名句都与饮酒有关;陶公还专门写有《饮酒》组诗二十首,为其“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而成,内容丰富,反映了作者许多方面的思想感情,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首更是陶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临死时,陶公还“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其一)。由此可见,饮酒对于陶渊明的人生及文学创作也就如饮酒对于李白一样有着特殊的、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比较的重点放在陶渊明身上,通过分析陶渊明饮酒诗与李白饮酒诗的差异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陶渊明的独特个性。
阅读陶渊明与李白的饮酒诗,可以发现两人的饮酒诗都可分为两个类型、两种情调。饮酒陶诗有的极为消沉苦闷,甚至陷于颓丧,如“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有的恬淡静穆,于平和中显出欣喜之情,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息动,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太白饮酒诗如《将进酒》、《梁园吟》、《襄阳歌》、《行路难》其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月下独酌》其二、三、四等给人的感觉是狂荡不羁、一泻千里、潇洒飘逸,如激流、峭壁、飓风,而《把酒问月》、《山中与幽人对酌》、《自遣》、《月下独酌》其一等作品则平和舒缓或者深沉宁静。就两人各自来说,两种情调的饮酒陶诗并不矛盾,从消沉苦闷到平和欣喜大略能看到渊明精神境界的提升过程,正如朱光潜所说“由冲突达到调和”;而李白的两种饮酒诗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难以想象这两种情调截然不同的作品出于同一人之手。其实不仅是饮酒诗,在全部太白诗中都存在着豪放狂傲与平和冲淡两种类型的作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李白诗歌的壮美和柔美两个方面,柔美即“清真”的风格,反映的是人类的普遍情感,而豪放狂傲的诗作极具个性化,表现了独一无二的李白本色。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比较陶、李二人饮酒诗的差异深入探讨二人个性的不同,从而有助于认识陶渊明的独特个性,所以属于“清真”诗风的太白饮酒诗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我认为,李白的“清真”饮酒诗与第二种情调的饮酒陶诗确实有非常相似之处,但这只是反映了人性的复杂性及太白诗风的丰富性,并不能以此为据否认太白饮酒诗与饮酒陶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故而本文中所说太白饮酒诗是只就其壮美风格而言的。
太白饮酒诗的基本风格是豪放、壮阔、狂傲,充斥着躁动不安的情绪,与作者一贯的艺术风格相一致;陶渊明饮酒则平缓、深沉、宁静,这也是陶诗的主要特点。可见不论陶渊明还是李白的饮酒诗在其各自的创作中都不是游离于主体风格之外的作品,二人的饮酒诗与其其他题材的诗作具有相同的艺术风格,亦是作者人生品格的写照,正如任何人都不会把太白想作渊明或把渊明当作太白一样,我们也决不会将二人的饮酒诗相混淆。李白的饮酒诗具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的雄壮气势,渊明却如“山涧清且浅”(《归园田居》其五)般小巧玲珑。李白酒量极大:“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斗酒十千恣欢谑”(同前)、“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美酒三百杯”(《月下独酌》其四)、“金樽清酒斗十千”(《行路难》其一),数字多以千百计,应是以巨盅狂灌豪饮;而渊明,“忽与一觞酒”(《饮酒》其一)、“一觞虽独进”(同前,其七)、“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一觞聊可挥”(《还旧居》),总是一杯一杯地小酌慢饮。太白心态之焦躁烦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其一),酒劲上涌以致失去理性,说出些不合逻辑的疯癫之语,如“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襄阳歌》)、“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月下独酌》其二),最后头晕脑涨、天旋地转,“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月下独酌》其三),要人“以水頮面”(洗脸)才能“稍解”(《新唐书》本传);而渊明不论是愁是喜饮酒时心态都平静深沉,愁饮他“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且进杯中物”(《责子》),乐饮他“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饮酒》其七)、“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他饮酒却从不醉酒,就算他说自己“既醉之后,辄题数句以自娱”(《饮酒》序)、“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五柳先生传》),但我想,就算渊明醉也是那种稍觉恍惚、微有酒意的小醉,却从不大醉,他始终神志清醒、思维明晰,在饮酒时进行人生、道德、生与死、短暂与永恒的哲理思考,于酒盅前悟到了许多道理:“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饮酒》其一)、“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同前,其二)、“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同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同前,其五)、“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同前,其七)、“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同前,其八)、“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同前,其九),当嗜酒变为“沉痼”,溺于其中无法自拔时,他反省道:“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荣木》)并发出了“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其二十)的慨叹,而且曾尝试戒酒(《止酒》诗)。由此可见,陶渊明是品酒,李白是醉酒,品酒者静、清、缓、沉,醉酒者动、浊、速、躁。清宋咸熙曰:“古之酒人,当以渊明为最,太白次之,若阮籍、刘伶,直是沉湎酣身矣。陶公《饮酒》诗,昭明太子所云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太白犹有胸中郁勃之气,其不如陶公者在此。渊明中行,太白狂者,身份有高下,出言亦如之,言为心声,信哉!”。
李白醉酒,飞荡飘舞、充满活力,屡屡有纵酒行乐之语但无颓废放荡之感,反而显出顽强热烈的生命力;渊明品酒,或消沉绝望、或淡泊欣喜,都显得轻柔软弱,要么被现实的苦难摧垮了:“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要么只有在放弃对生命的眷恋、不再在乎生死的时候才能获得快乐:“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同前,其十四)“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同前,其十五)可见,李白的饮酒始终是昂扬、有力量、乐观的,陶渊明的饮酒却总是低沉、软弱、悲观的,两人的饮酒诗不论艺术风格还是思想情调都是截然相反的。
陶、李二人饮酒都是因为心中痛苦,故而借酒浇愁。李白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高歌取醉欲自慰”(《南陵别儿童入京》)、“古人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同前)、“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同前)、“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月下独酌》其四)的诗句,陶渊明也写过“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还说“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朱光潜说:“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底(的)苦闷,忘去世间种种不称心底(的)事。”不过正如二人饮酒的情调迥异,他们愁苦的原因也是截然不同的。
李白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是以政治家自居的,他的人生追求始终都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所以李白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政治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求得政治上的成功。和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家一样,李白的本意并不是要作文学家、以诗歌留名后世,文学对于他来说,是扩大影响、使自己名闻天下的手段和工具,是娱情的爱好,也是排遣苦闷的方法,却不是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好炫耀的李白几乎从不炫耀自己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屡屡自夸的都是自己的政治才干。因此,追求政治功名受挫是李白痛苦的根源,为了化解心中巨大的痛苦,他便纵酒放诞。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载,白在宫廷时,“帝用疏之”,他就“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后来被从宫中“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旧唐书》本传)在酒后狂醉中写下的诗篇里他总是发布这样的言论:“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梁园吟》)、“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月下独酌》其四),还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赞美隐士的生活。其实这些都是气话、反话、假话,他正是因为太看重政治功名、圣贤节操,总也不能忘怀,所以愈得不到就愈悲伤,以致靠诅咒来发泄一下愤懑,说过之后气消了便又振作精神投入到追求政治功名的现实斗争中去了。这种“追求-幻灭-发泄-继续追求”的过程可以说是李白一生的一种循环模式,也是他许多著名诗篇的感情套路,像《襄阳歌》、《梁园吟》、《将进酒》、《月下独酌》其二、三、四、《行路难》其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作品都是这样的。从李白的饮酒诗里可以看到他真实的文学才能和真实的痛苦,但却看不到他真实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因此李白是假喝酒,最后说气话、反话、假话,甚至疯话。他饮酒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买醉、忘忧,借酒浇愁发泄过后,心中的矛盾痛苦暂时得到了化解,又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力量了,他就将酒杯弃置一旁,不再需要酒了。但是他饮酒后写下的诗篇因其狂荡的气势、恣溢的文采使人们折服,但其饮酒诗和饮酒的行为本身并没有陶渊明那样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寄托。
陶渊明饮酒最初也许与李白一样仅仅是为了浇愁,但渊明痛苦的原因既与李白不同,他对于饮酒的态度又有过两次转变——抑或说是两次精神境界的提升——使渊明从“忧愁饮酒”到“欣喜饮酒”,最后“超越饮酒”。
渊明对于政治的态度与李白正相反,他毫不热衷政治,从来就不想做官。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杂诗》其八)、“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自诩(《五柳先生传》)。因此渊明从来不是一个政治的人,古人、今人多有搬出晋宋易代几十年间政治大事(如司马道子、元显父子的擅权,桓玄的谋逆,刘裕的篡位等等)来解释陶诗者,但渊明自己从来没提过这些事,他在当时根本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像李白与上流社会乃至皇帝本人都有密切往来;他认识的官员最高是刺史,最多不过是一面之交,常常往来的不是农民就是西曹、贼曹、主簿、长史这样的州县小吏,高层的政治斗争和陶渊明是毫不相关的,除了那首至今还解不通的《述酒》外在陶诗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关心国家大事。因此,研究陶诗及渊明的为人尽可也应须抛开政治因素。渊明的痛苦,我认为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他大概有一种天生的内向性格,多愁善感、优柔寡断,又非常恋家,参与社会生活、奔波行役对他来说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及《杂诗》其九、十、十一中以那么凄苦的笔调抒写了旅途行役之苦,并表达了对于居家生活的强烈眷恋。在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是担任公职、作社会人他就痛苦,而只要能够回到家里过远离社会交往的生活他就快乐。他向往的是“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田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的生活,但或者是因为贫困、或者是为了家族利益,抑或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他“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园田居》其一),“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其一),这种违背心意的生活使他觉得“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杂诗》其三)。其二,性格内向、不喜交际的人往往好沉思,渊明亦然。他常常思考生与死、人生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命运的幸与不幸这种沉重的问题。据我统计,今存陶诗一百二十四首(未计联句一首及桃花源诗)中涉及生与死哲理思考的有四十七首,占三分之一还多,而这个统计是只就字面上直接出现有关生与死的内容为据的,虽没有明确提到但品味诗意可知渊明确实是在思考生死问题的作品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估计比饮酒诗还多,陶诗几乎是篇篇含有生与死的思考。“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其一)、“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其十五)、“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其一)……渊明是不相信灵魂不灭的,他用相当多的诗句反复述说着同一个道理:人一死就归于虚无,任何人也逃不过这可悲又可怕的命运。这使他非常痛苦:“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因为有这两种痛苦,渊明曾经一度沉溺于酒中,“得酒莫苟辞”(《形影神·形赠影》)、“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同前,其四),“酒对于他仿佛是一种武器,他拿在手里和命运挑战”,此为陶渊明“忧愁饮酒”的阶段,第一种情调的饮酒陶诗多是此时所作。虽则愁苦的原因不同,但就对于酒的态度来说此阶段的渊明与李白并无两样,无非是把酒当作解愁的工具,在酒中求得精神的麻醉以缓解内心的痛苦,其饮酒的行为并没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寄托。不过因为渊明性格的温和、脆弱,不似激烈的李白狂灌豪饮,写下的饮酒诗汪洋恣溢、气势壮阔,如狂风暴雨,而是小杯慢饮,其饮酒诗深沉宁静、轻柔温蔼,如连绵细雨;也不像坚强乐观的李白尽情发泄了愤懑之后就振作起来,又投入到现实斗争中去,而是一味地陷在悲观消沉中,愈饮愈愁,无以自拔。
由于渊明如此饮酒,嗜酒“变成一种沉痼,不但使他‘多谬误’,而且耽误了他的事业,妨害他的病体”,于是渊明进行了自省:“嗟予小子,禀兹固陋。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矣,怛焉内疚。”(《荣木》)作《止酒》以自警。与此同时,因为他如此悲伤,想到“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其一)、“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其五),而自己又“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园田居》其一),感到非常委屈,产生了一种自怜自爱的感情,于是“及时当勉励”(《杂诗》其一),终于打消了一切顾虑,彻底脱离了现实社会,归隐田园,过自己梦寐以求的隐居耕读的生活,由此获得了良心的平静,也得到了真正的快乐,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归隐之后,渊明的生活内容简单、淳朴又富于情趣,主要是耕作、读书、课子、会友、郊游,而饮酒是贯穿于所有这些生活内容中的一件事。在渊明后半生里,酒融入了他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已经成为渊明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生活中的每一天都离不开酒,不论遇到什么事都会饮酒:悲伤时,他“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三);欣喜时,他“漉我新熟酒”(《归园田居》其五);耕作后,他“壶浆劳近邻”(《癸酉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收获了,他“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搬新家,他“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还旧居,他“一觞聊可挥”(《还旧居》);见幼子顽劣,他“且进杯中物”(《责子》);观孩童可爱,他“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其一);与朋友一起,他“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独自一人时,他“浊酒聊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时,饮酒对于渊明已不仅仅是浇愁的手段,而有了一种永恒的意义。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真意就是人生的真谛。而他还说过:“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王瑶释“会”为“理之所在”。我认为此之“会”即彼之“真意”,渊明在隐居田园的生活中体悟到了人生、自然、宇宙的真知大道,所以欢喜地持杯畅饮。此为渊明“欣喜饮酒”的阶段,饮酒是和归隐田园的人生选择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越饮酒就越脱离社会、越坚定了作隐士的决心、越能于田园生活中发现幸福,第二种情调的饮酒陶诗都写于此时。他说“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其七),又说“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同前,其九),饮酒可算是渊明终极精神追求的具象表现,他在归隐田园中、也是在饮酒中感觉到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归宿的欣喜,所以他说:“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
在渊明最富于哲理的作品《形影神》三首中可以看到他由“忧愁饮酒”转入“欣喜饮酒”的过程,《形赠影》是他借酒浇愁、沉溺酒中的写照,因为如此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便有了影对形的批判(《影答形》),这表明渊明已经进入“欣喜饮酒”的阶段,以影所主张之“立善求名”代替形所说之纵酒行乐。这里应注意,渊明心目中之“立善求名”非名教中人所言之“善”、“名”:渊明的“善”是自己良心的安宁,不求彰显于众人,渊明之“名”是建立在自己良心安宁基础上的道德名节,而非他所批判的“但顾世间名”(《饮酒》其三)。渊明归隐田园并不是放弃了善名,而是要在最诚实、最问心无愧的境界上成全它。他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同前,其十),清何焯评曰“恐坠固穷之节也”,可见渊明还是追求善名的,他的隐居、躬耕、固穷都为了做到名实相符、表里如一,他人是可以欺骗的,但自己不可能欺骗自己,所以陶渊明追求的善名和伪君子追求的虚名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因为渊明也求名就把他和名教众人等同起来,否定他作为真隐士的伟大,或因为渊明是真隐士就不承认他也求名。
在“忧愁饮酒”时,渊明处在一种非道德的境界,“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对于人生他采取的完全是不顾一切、及时行乐的颓废态度,到“欣喜饮酒”时,他就转入了完善道德的境界,过自己认为是人生真谛的生活。而在成为道德完人(成圣)之后渊明的精神境界又提高到超越道德的境界(成神),就是《神释》中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境界,如同中国古代哲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亦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人生四种境界之最高者的“天地境界”。这种境界,按庄子的话说就是:“丧我”(《庄子·齐物论》)、“心斋”(《庄子·人间世》)、“坐忘”(《庄子·大宗师》),按孔子的话说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或如佛教所说的“空”、“禅定”、“涅盘”。渊明自己也有诗曰:“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其十四)这就是渊明“超越饮酒”的饮酒,这时他饮的已不是物质的酒本身,而是在忘却自我、与天地相合的超脱境界中显现出的“深味”。我认为,这“深味”是比“真意”、“会”更高层次的人生、自然、宇宙的真知大道:“真意”、“会”是属人的,是崇高的道德,而“深味”是属神的,已超越了人间的道德,与自然万物化为一体。鲁迅说诗人“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但陶渊明正如许多哲学家、宗教家一样达到了这种境界,不过在这样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诗人了,当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时并没有真正地“忘言”,因为还有这两句诗用人的语言写了出来,而在超越人间的道德、臻于化境的境界中渊明真的“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得意忘言”(《庄子·外物》)了。所以渊明在他一生中的三种精神境界下相应地有三种境界的饮酒,但却没有第三种饮酒诗。
朱光潜说:“渊明和许多有癖好(指饮酒)的诗人们(例如阮籍、李白、波斯的奥马康颜之类)的这种态度,在近代人看来是‘逃避’,我们不能拿近代人的观念去责备古人,但是‘逃避’确是事实。”李白饮酒消愁是逃避现实,但他消愁后的结果是继续介入现实,故而他的逃避是暂时的,是假逃避,酒后所说的也都不是真心话;而渊明是真逃避,在饮酒中长久地脱离了现实,不论是哪种境界的饮酒,渊明都是转入内心生活、在个人世界里寻求解脱,他是“酒后吐真言”,不管悟到的是“真意”、“会”还是“深味”,他饮酒诗中所说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陶、李二人的饮酒、饮酒诗正如他们的思想、性格,差异巨大:李白是自信、骄傲、豪放、乐观的,陶渊明是内向、自卑、软弱、悲观的,李白有强大的生命活力而缺少沉思自省的深度,渊明的思考非常深刻沉重,而正因为这种沉重、再加上天性的脆弱,使他“每每多忧虑”(《杂诗》其五)、“气力不及衰”(《还旧居》),总显得病弱无力。
参考资料:陶渊明与李白的饮酒诗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9-09-07
陶渊明,众所周知,是一名隐士,看淡了名利红尘,所以充满了飘逸的气息。饮酒只为自娱自乐,感受乡村,赞美自然。
李白则是豪放之士,而且他的仕途不太如意,所以他饮酒一般有两种:一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二是心情愉悦时大气的表现。
这只是我个人的浅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李白则是豪放之士,而且他的仕途不太如意,所以他饮酒一般有两种:一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二是心情愉悦时大气的表现。
这只是我个人的浅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