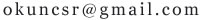葛红兵:我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现在做大学教师。我今天主要不是想谈自己,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想借这个机会主要谈谈教育问题,新浪是一个强势媒体,我今天在这里说说我最近特别想说的话。多年前我曾经着力于研究中国户口问题,写过大量的文章,在中国高层的内部论坛发布,也参加过全国妇联、公安部等等搞的户口问题的座谈会。那个时候我认为中国社会的户口问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导致中国社会城乡的割裂,构成城乡的二元结构。它是导致中国社会不同的人有不同命运的一个重要根源。最近我们看到中国户口问题已经有所改变了,在浙江和江苏的苏南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甚至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成为一个限制了,有的地方已经取消城乡户口的差别。 现在我感觉到我们的不公平是什么呢?主要一个是在教育方面,这是我今天想谈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城乡教育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不对等。比如说在我的故乡,一个城市里面,城里的孩子和与他咫尺之遥的孩子办学的条件相差很大。我父母所在的农场有上万的职工,每年有几十人初中高中毕业,但是能够正常升学和升入大学的屈指可数。不是这些孩子智力上跟不上,而是这些孩子没有获得平等的教育条件。我今天来第一个想在这里做一个重要的呼吁,就是可以控制城乡的差别。城里人应该有义务和责任帮助乡村的孩子们,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他们的办学条件,也提高他们的师资水平。如果说“人生而平等”的话,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涵现在在中国现在已经不是户口问题了,而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一个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我今天想为农村的孩子做一个呼吁,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大家都关心孩子,最需要关心的是那些农村的孩子们。我希望新浪能够允许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对社会发出一个呼吁。
葛红兵:我今天想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我觉得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教孩子共性,比如说教给他社会的普遍伦理,普遍的知识,普遍的机能。比如说一个技工的才能,一个工程师的才能,一个科学家的才能,一个艺术家的才能,然后交给他普遍的人伦,孝敬父母等等,这是教育的一个目的,让他能在社会立足。
第二个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教孩子个性。我们都知道人在启蒙时期接受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科学家说过,所谓启蒙就是教人自我决断,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决定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氛围、还是学校里的老师,整个社会都重视孩子的共性培养,比如说他的知识,他求生技能等等,对他们个性东西却很少培养。有时我们甚至害怕他们的个性,当孩子说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跟我们日常生活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我们是感到害怕的。我们害怕孩子提出跟我们教材不同的观念,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审美观有差异,害怕孩子跟主流有距离,这正是我们教育一个很大的弊端。在我看来,教育最重要的、也是根本性的目的,是孩子的自我决断,就是培养孩子的个性。我看来,一个孩子有自我意识、有自己个别性的观点、个人性的观点,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有自我,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最好的事情,说明这个孩子的培养已经到位了,这个应该是家长为之感到高兴的事情。一个特立独行的孩子,在启蒙阶段也需要成年人对他进行引导,就是要教给他普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99%的事情还应该给孩子自觉权。我们都知道,求知是人的本能。人在什么时候感觉最为恐惧,最为不安,最为焦虑?就是未知的情况下。比如今天我在路上堵车,我不知道前面堵了多少车,我就感到非常不安,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说前面有五辆车,有三个红灯,我知道了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也就是说在未知的情况下,人最有本能的反应。 但是,恰恰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丧失了这种对未知的兴趣,关键在什么呢?还是要回到共性和个性的培养目标上。我们绝大多数的老师和家长都试图给孩子一个普遍共性的东西,却没有照顾到孩子个性的需求。比如说小孩子在做完这道数学题以后,他希望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他自己感兴趣的那些方面,比如说3D动画设计——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已经考取3D动画学院,如果我们老师压抑了这个,一定要他把数学题反复的操练,这样这个孩子就会对数学失去兴趣,对语文失去兴趣。然后又不能发现3D的兴趣——表面上好象他是没有兴趣的。这样就使我们孩子失去了本能的、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对于未知世界的焦虑。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情况还是要从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目前教育的观念、包括家长的观念来着手。 我们总强调“一律”,就是所有孩子要遵守同一个纪律、做同一种习题、达到一个目标、做一类孩子,我们给孩子施加的目标太统一了。什么叫做统一呢?我参加过一个中学的观摩,有一个教育课,初一的孩子,班上所有孩子都想说我想作科学家,我想做学者,我想作什么,没有一个孩子说我想做技术工人,我想做一个农民,我想种菜、看上去又美、吃上去味道鲜美的菜,没有!为什么?我们整个社会都给所有的孩子设计了一个5%的孩子才能达到的目标,使100%的孩子沿着那5%的路走,这样扼杀了孩子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扼杀使我们人才的标准和人的发展变成统一化,不利于我们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多样性的发展,使我们整个社会也趋于单调,知识结构一致、行为模式一致、伦理价值原则一致、一切都很一致。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趋同性的社会——我们的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整体上这种全社会对孩子水平理想要求过高,使我们教育看起来变成了对孩子的折磨。因为我们设计的目标模式实际上只有5%的人才能达到,95%达不到,是这个状态锻造了我们整体的社会氛围。新加坡社会经济条件比我们好很多,他完全可以普及大学,但是恰恰相反,新加坡一个大城市只有两所大学,它只有一部分的同学能够进入大学,绝大多数进入的是技术教育学院。为什么呢?新加坡社会对孩子这种教育是非常可取的,他知道每一个孩子有每一个孩子自己的道路,每一个孩子应该有适合他自己的理想和前途,他应该在社会上找到个性化的地位和生活姿态。所以,它没有鼓励每一个孩子都做科学家,都去读大学,都成为精英。
第一个,我们的全球意识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地球教育根本没有跟上,我们的爱只是教到爱你的祖国为止,从爱亲人开始,爱故乡到爱你的祖国就为止了,没有教到爱地球、爱人类这样的地球意识。 第二个,我们是从东西对立这样一个观念发展而来的,从两大阵营对立意识发展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痛恨,比如说对日本,对美国人。那么我们看到,我在新加坡也待过,在泰国也待过,在印度尼西亚待过,这些国家在二战中也受过严重的侵害,他们的侵害不低于中国,但是中国人对日本的痛恨远远深于他们,我们受到的是仇恨的教育。第三个,我觉得我们是以阶级斗争立国的。1949年革命以后,强调人与人的斗争,而不是普遍的爱。由此我想到顾准给孩子写信,因为顾准当时是受到镇压的,妻子跟他划清界限,他说“你们给我造成的痛苦我原谅你们,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也希望你们原谅。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见我最后一面。”顾准也有存款给孩子,但是顾准自己的孩子全部拒绝。这种情况跟俄罗斯发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恨的教育是很严肃的,但是对爱的教育却往往是模糊的。恰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和解,阶级的和解也好、国家的和解也好,比阶级对立,国家对立更加重要。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宽容意识、和解意识、普遍的人类意识。这个方面我们教育是最欠缺的。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上来,我希望我们家长给孩子去读更多这方面的书。如果从这方面来出发,我希望我们家长可以给我们孩子读一些传统的典籍,岳簏书社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我们是非常强调“仁”的,这个是一个抽象的爱,是一个大爱。我们一个期间批判过的,但是现在我们孩子可以去读它。我们也不愿意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宗教教徒或者什么,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宗教当中汲取爱的力量,爱的精神养料。比如说圣经新约这样的书,我们可以当做知识养料的书让孩子读,这一系列的书也是我们更加需要的。
葛红兵:这个也是我今天来之前想的一个重要题目,就是我们对孩子应该怎样的看待。在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一个引文,就是引用爱迪生的那句话,“对一个成功的人而言99%是汗水,1%是灵感。”实际上后半句给省略掉了:“恰恰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教育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可以从事创造性工作,比如说科学家、艺术家这种工作的人,只有5%左右。95%的人能够从事机械工程等等这样的工作。他也告诉我们,人的确存在着重大先天区别,我们要承认这个先天区别。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强调的是理想主义教育,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小学教育面临危机,其中有一个危机就是理想主义教育危机,我们所有人都想作5%的人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实际上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中学老师说的很好,不能够要求所有人都做第一名,应该给每个孩子确立一个他能达到的目标。中学的老师应该有能力帮助孩子确立自己的目标,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所以,我每年招研究生以后,招进来第一句话,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在我这里做什么,比如说我给你布置一个学术课题,你一定要把它做的多好,或者过几年你读博士等等这些目标。是你到这里以后,我能够帮助你找到自己,你在本科阶段没有找到自己,你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不知道你人生能够寄托在什么上面,你做这个事情感到快乐,也许你未来可以成功,甚至于不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是快乐的,你觉得过程已经有价值了。到我这里来,我希望这三年,在我们一起讨论、研究、阅读等等这些过程让你找到你的人生定位,帮助你完成对自我的认识,形成对自我的要求,当然是跳一跳才能达到那个要求,我就感到很满足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把整个的教育观念颠过来,我们现在是设立一个目标,让所有的孩子都去达到,所有孩子去做同一类的事。我现在要说的是反过来,我们的教育应该帮助孩子自己确立亿亿万万不同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认识,教育应该帮助他形成这种自我决断、自我认识,帮助他完善自我个性。如果教育观念做了这样一个转变,我们这个社会感觉自我不成功的、感觉人生失败的人就会少很多。
我有一个很好的初中老师,他教会我怎么观察一个杯子,一棵树,而且你还要看到他是个活的生命。你看这个茶杯立在那里还不对,你要看到他里面还有半杯水,他里面还有热气,这个光半部是亮的,半部是暗的,你要看到这些东西。他给我介绍很多童话,我看了《快乐王子》,因为我在初中里学的,有一个很差的雕塑,就是为了几头羊献身的两个女孩子,我就把他想成我的快乐王子,就是为人类献身的,我想我将来可以写这样的东西就好了。后来我就渐渐写小说和散文,后来也不断的发表。但是我中间也有曲折,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我的一个同学,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的诗歌写得太好了,简直是高不可及的范本。我想他比我只大一岁,我都比不上他,我想我还有什么出息呢。后来我就转向文艺理论研究,后来就成了一个批评家。但是当我成了一个批评家以后,我对我们当代小说散文诗歌的状况又开始不满起来,对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诗歌创作、散文创作也开始不满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些过那个“悼词”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可以继续写下来。所以95、96年我又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99年我就完成了大家认为是我的成名作《我的N种生活》。之前我还些过两个科幻长篇,当时印了9万多套,如果说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96年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了。后来还有一个科幻长篇《未来战士三部曲》。2003年我又出了《沙床》这样的书。实际上我也在渐渐跟自己搏斗,如果我写散文、写小说是跟自己进行心灵的对话,安慰自己情绪的过程。比如说我的N种生活对我精神状况的一次超脱了,写沙床也是这样的,是我碰到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碰到亲人的病,我自我说服,和自己谈心的。写哲学专著是为了思考一个问题,把一个问题想清楚。所以,很多人看起来我好象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之间是摇摆的,实际上对我来说这两者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困惑。也有很多人看到我在学术研究上也是摇摆的,比如说多年前我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面世的,后来我又变成了一个文艺理论家,好象是从批评转向了文艺理论。实际上批评和文艺理论是一块的。近年我又转向哲学人类学,但是哲学人类学与文艺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文艺学到了高端,实际上他对人审美性超越的研究,人在这个世界上有限的生活里,如何追求无限永恒的世界,这个就带来人类的思考。这种道路在我们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康德,他的研究最后导致是人类学,海德格尔都有这种阶段的。最典型的是尼采,他从审美研究语言形容到最后成了一个哲学家,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葛红兵:我一直有这个冲动,就是前年我跟我的朋友几个人设计一套丛书,就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因为我真是有很多的体验,也试图搞一个对话、把我们的教育想法都结合起来。但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在国外,有的在国内,有的在欧洲,有的在亚洲其他国家,很难聚到一起。我自己也一直有这样一个冲动。这次我出一个对话集叫做《直来直去》的时候,就是想把自己的观念更多的容纳进去。一个是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谈,第二个直接谈我教育观念,第三通过我对一些文化名人的解构做一个“去神”的工作,最后谈谈整体我对中国思想史、就是国家观念等等这样一些的看法。当然你们看的时候有的地方需要这样那样切,切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这个也是迫不得已的。
葛红兵:他们都是不错的作家,石康是不错的。安尼有几部城市女性题材的小说,我觉得都不错。也写过关于石康批评的意见,我觉得整体中国作家缺乏一个第三维,就是超越人类意识、地球意识、宇宙意识这一维,这种普遍爱的一维。为什么我们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可以反复读反复感动?他们的作品有这种精神的力量,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人道主义广泛的同情,有这种意识,有超越国家、超越有限生活,去寻求永恒的意味愿望在里面。我就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欠缺的。那么鲁迅我觉得他是中国少有、对人生活做出决绝批判的作家,所以我们看到鲁迅是非常悲观的,为什么。他看到人世生活的有限性,看到人性上的有限性,看到了这些东西。但是,鲁迅依然没有完成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超越,他晚年写到过他,我觉得鲁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人的生活是无望的、人的生活是阴暗的,但在另外一条线还有一个阳光的东西在那里,作家可以揭示出来,鲁迅意识到了,但是生命没有给他时间。我觉得在中国的诗人当中穆旦、海子是比较少有的有超越意识的作家,这也是诸多读者读《沙床》时误解我的原因。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所以我们很难理解那种超越性的追求。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追求以灵魂给人安慰这样的精神世界,我追求的是这样一个东西,无神论者认为这个是虚伪的,有神论者认为这个还不够。中国作家在这个一维度里探索还不够,整体是不够的。
葛红兵:还是最开始的话,我希望能够呼吁大家重视农村教育的问题、重视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配置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社会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比如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城里面的小学跟乡下的小学是不是可以搞更多教师之间的互相交流。比如说结对性的教师之间互派,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仅在硬件方面帮助乡下小学提高,也在软件上帮助乡下小学提高。这个可以给我们孩子以更多的出路。我觉得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此负有更多的责任,应该站出来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呼吁。我觉得许多的人都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就像钱钟书说的那样,躲起来像鸵鸟一样,对呼吁那些人觉得他们是作秀、无聊,我觉得对这种事情我感到非常伤感。如果所有人都不来说这个事情,那么谁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社会整体性对这个不平等的麻木、视而不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我想谈教育观念整体上的突破。我觉得我们功利教育太多,非功利人道主义的教育、人类意识的教育、地球意识的教育太少。 最后我们教育观念要回到对孩子个性的尊重、个性的培养,培养千差万别的孩子,不是把孩子造成统一的一个模式,往模式里套,也希望这个社会的教育观念有一些变化。最后我想孩子们。实际上我一直在教育的领域里工作,关于911那次的现场社会调查给我的打击非常沉重,我一点都没有夸张这个说法。他也使我开始把我自己的重心也慢慢转移到这里面。以前中学请我演讲我是拒绝的,大学请我演讲我也拒绝,后来所有中学邀请我都接受,大学我也大部分都是接受的,还出了一本演讲集。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这个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我们孩子有欠缺,这是知识分子的欠缺,他们没有把孩子教好,我希望大家都应该来做这个事情。
葛红兵:我今天想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我觉得教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教孩子共性,比如说教给他社会的普遍伦理,普遍的知识,普遍的机能。比如说一个技工的才能,一个工程师的才能,一个科学家的才能,一个艺术家的才能,然后交给他普遍的人伦,孝敬父母等等,这是教育的一个目的,让他能在社会立足。
第二个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教孩子个性。我们都知道人在启蒙时期接受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科学家说过,所谓启蒙就是教人自我决断,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决定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氛围、还是学校里的老师,整个社会都重视孩子的共性培养,比如说他的知识,他求生技能等等,对他们个性东西却很少培养。有时我们甚至害怕他们的个性,当孩子说一个不一样的观点、跟我们日常生活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我们是感到害怕的。我们害怕孩子提出跟我们教材不同的观念,我们害怕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审美观有差异,害怕孩子跟主流有距离,这正是我们教育一个很大的弊端。在我看来,教育最重要的、也是根本性的目的,是孩子的自我决断,就是培养孩子的个性。我看来,一个孩子有自我意识、有自己个别性的观点、个人性的观点,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有自我,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最好的事情,说明这个孩子的培养已经到位了,这个应该是家长为之感到高兴的事情。一个特立独行的孩子,在启蒙阶段也需要成年人对他进行引导,就是要教给他普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99%的事情还应该给孩子自觉权。我们都知道,求知是人的本能。人在什么时候感觉最为恐惧,最为不安,最为焦虑?就是未知的情况下。比如今天我在路上堵车,我不知道前面堵了多少车,我就感到非常不安,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说前面有五辆车,有三个红灯,我知道了就不会有这种恐惧感。也就是说在未知的情况下,人最有本能的反应。 但是,恰恰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丧失了这种对未知的兴趣,关键在什么呢?还是要回到共性和个性的培养目标上。我们绝大多数的老师和家长都试图给孩子一个普遍共性的东西,却没有照顾到孩子个性的需求。比如说小孩子在做完这道数学题以后,他希望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他自己感兴趣的那些方面,比如说3D动画设计——我有一个同事的孩子已经考取3D动画学院,如果我们老师压抑了这个,一定要他把数学题反复的操练,这样这个孩子就会对数学失去兴趣,对语文失去兴趣。然后又不能发现3D的兴趣——表面上好象他是没有兴趣的。这样就使我们孩子失去了本能的、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对于未知世界的焦虑。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情况还是要从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目前教育的观念、包括家长的观念来着手。 我们总强调“一律”,就是所有孩子要遵守同一个纪律、做同一种习题、达到一个目标、做一类孩子,我们给孩子施加的目标太统一了。什么叫做统一呢?我参加过一个中学的观摩,有一个教育课,初一的孩子,班上所有孩子都想说我想作科学家,我想做学者,我想作什么,没有一个孩子说我想做技术工人,我想做一个农民,我想种菜、看上去又美、吃上去味道鲜美的菜,没有!为什么?我们整个社会都给所有的孩子设计了一个5%的孩子才能达到的目标,使100%的孩子沿着那5%的路走,这样扼杀了孩子多样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扼杀使我们人才的标准和人的发展变成统一化,不利于我们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多样性的发展,使我们整个社会也趋于单调,知识结构一致、行为模式一致、伦理价值原则一致、一切都很一致。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趋同性的社会——我们的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整体上这种全社会对孩子水平理想要求过高,使我们教育看起来变成了对孩子的折磨。因为我们设计的目标模式实际上只有5%的人才能达到,95%达不到,是这个状态锻造了我们整体的社会氛围。新加坡社会经济条件比我们好很多,他完全可以普及大学,但是恰恰相反,新加坡一个大城市只有两所大学,它只有一部分的同学能够进入大学,绝大多数进入的是技术教育学院。为什么呢?新加坡社会对孩子这种教育是非常可取的,他知道每一个孩子有每一个孩子自己的道路,每一个孩子应该有适合他自己的理想和前途,他应该在社会上找到个性化的地位和生活姿态。所以,它没有鼓励每一个孩子都做科学家,都去读大学,都成为精英。
第一个,我们的全球意识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我们的地球教育根本没有跟上,我们的爱只是教到爱你的祖国为止,从爱亲人开始,爱故乡到爱你的祖国就为止了,没有教到爱地球、爱人类这样的地球意识。 第二个,我们是从东西对立这样一个观念发展而来的,从两大阵营对立意识发展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痛恨,比如说对日本,对美国人。那么我们看到,我在新加坡也待过,在泰国也待过,在印度尼西亚待过,这些国家在二战中也受过严重的侵害,他们的侵害不低于中国,但是中国人对日本的痛恨远远深于他们,我们受到的是仇恨的教育。第三个,我觉得我们是以阶级斗争立国的。1949年革命以后,强调人与人的斗争,而不是普遍的爱。由此我想到顾准给孩子写信,因为顾准当时是受到镇压的,妻子跟他划清界限,他说“你们给我造成的痛苦我原谅你们,我给你们造成的痛苦也希望你们原谅。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见我最后一面。”顾准也有存款给孩子,但是顾准自己的孩子全部拒绝。这种情况跟俄罗斯发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恨的教育是很严肃的,但是对爱的教育却往往是模糊的。恰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和解,阶级的和解也好、国家的和解也好,比阶级对立,国家对立更加重要。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宽容意识、和解意识、普遍的人类意识。这个方面我们教育是最欠缺的。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上来,我希望我们家长给孩子去读更多这方面的书。如果从这方面来出发,我希望我们家长可以给我们孩子读一些传统的典籍,岳簏书社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我们是非常强调“仁”的,这个是一个抽象的爱,是一个大爱。我们一个期间批判过的,但是现在我们孩子可以去读它。我们也不愿意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宗教教徒或者什么,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宗教当中汲取爱的力量,爱的精神养料。比如说圣经新约这样的书,我们可以当做知识养料的书让孩子读,这一系列的书也是我们更加需要的。
葛红兵:这个也是我今天来之前想的一个重要题目,就是我们对孩子应该怎样的看待。在我们中学的课本里有一个引文,就是引用爱迪生的那句话,“对一个成功的人而言99%是汗水,1%是灵感。”实际上后半句给省略掉了:“恰恰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教育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可以从事创造性工作,比如说科学家、艺术家这种工作的人,只有5%左右。95%的人能够从事机械工程等等这样的工作。他也告诉我们,人的确存在着重大先天区别,我们要承认这个先天区别。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强调的是理想主义教育,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小学教育面临危机,其中有一个危机就是理想主义教育危机,我们所有人都想作5%的人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实际上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中学老师说的很好,不能够要求所有人都做第一名,应该给每个孩子确立一个他能达到的目标。中学的老师应该有能力帮助孩子确立自己的目标,帮助孩子认识自己。所以,我每年招研究生以后,招进来第一句话,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在我这里做什么,比如说我给你布置一个学术课题,你一定要把它做的多好,或者过几年你读博士等等这些目标。是你到这里以后,我能够帮助你找到自己,你在本科阶段没有找到自己,你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不知道你人生能够寄托在什么上面,你做这个事情感到快乐,也许你未来可以成功,甚至于不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是快乐的,你觉得过程已经有价值了。到我这里来,我希望这三年,在我们一起讨论、研究、阅读等等这些过程让你找到你的人生定位,帮助你完成对自我的认识,形成对自我的要求,当然是跳一跳才能达到那个要求,我就感到很满足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把整个的教育观念颠过来,我们现在是设立一个目标,让所有的孩子都去达到,所有孩子去做同一类的事。我现在要说的是反过来,我们的教育应该帮助孩子自己确立亿亿万万不同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认识,教育应该帮助他形成这种自我决断、自我认识,帮助他完善自我个性。如果教育观念做了这样一个转变,我们这个社会感觉自我不成功的、感觉人生失败的人就会少很多。
我有一个很好的初中老师,他教会我怎么观察一个杯子,一棵树,而且你还要看到他是个活的生命。你看这个茶杯立在那里还不对,你要看到他里面还有半杯水,他里面还有热气,这个光半部是亮的,半部是暗的,你要看到这些东西。他给我介绍很多童话,我看了《快乐王子》,因为我在初中里学的,有一个很差的雕塑,就是为了几头羊献身的两个女孩子,我就把他想成我的快乐王子,就是为人类献身的,我想我将来可以写这样的东西就好了。后来我就渐渐写小说和散文,后来也不断的发表。但是我中间也有曲折,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我的一个同学,他只比我大一岁,他的诗歌写得太好了,简直是高不可及的范本。我想他比我只大一岁,我都比不上他,我想我还有什么出息呢。后来我就转向文艺理论研究,后来就成了一个批评家。但是当我成了一个批评家以后,我对我们当代小说散文诗歌的状况又开始不满起来,对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诗歌创作、散文创作也开始不满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些过那个“悼词”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可以继续写下来。所以95、96年我又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99年我就完成了大家认为是我的成名作《我的N种生活》。之前我还些过两个科幻长篇,当时印了9万多套,如果说我是一个畅销书作家,96年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了。后来还有一个科幻长篇《未来战士三部曲》。2003年我又出了《沙床》这样的书。实际上我也在渐渐跟自己搏斗,如果我写散文、写小说是跟自己进行心灵的对话,安慰自己情绪的过程。比如说我的N种生活对我精神状况的一次超脱了,写沙床也是这样的,是我碰到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碰到亲人的病,我自我说服,和自己谈心的。写哲学专著是为了思考一个问题,把一个问题想清楚。所以,很多人看起来我好象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之间是摇摆的,实际上对我来说这两者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困惑。也有很多人看到我在学术研究上也是摇摆的,比如说多年前我是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面世的,后来我又变成了一个文艺理论家,好象是从批评转向了文艺理论。实际上批评和文艺理论是一块的。近年我又转向哲学人类学,但是哲学人类学与文艺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文艺学到了高端,实际上他对人审美性超越的研究,人在这个世界上有限的生活里,如何追求无限永恒的世界,这个就带来人类的思考。这种道路在我们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康德,他的研究最后导致是人类学,海德格尔都有这种阶段的。最典型的是尼采,他从审美研究语言形容到最后成了一个哲学家,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葛红兵:我一直有这个冲动,就是前年我跟我的朋友几个人设计一套丛书,就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因为我真是有很多的体验,也试图搞一个对话、把我们的教育想法都结合起来。但是我们现在有的人在国外,有的在国内,有的在欧洲,有的在亚洲其他国家,很难聚到一起。我自己也一直有这样一个冲动。这次我出一个对话集叫做《直来直去》的时候,就是想把自己的观念更多的容纳进去。一个是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来谈,第二个直接谈我教育观念,第三通过我对一些文化名人的解构做一个“去神”的工作,最后谈谈整体我对中国思想史、就是国家观念等等这样一些的看法。当然你们看的时候有的地方需要这样那样切,切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这个也是迫不得已的。
葛红兵:他们都是不错的作家,石康是不错的。安尼有几部城市女性题材的小说,我觉得都不错。也写过关于石康批评的意见,我觉得整体中国作家缺乏一个第三维,就是超越人类意识、地球意识、宇宙意识这一维,这种普遍爱的一维。为什么我们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可以反复读反复感动?他们的作品有这种精神的力量,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人道主义广泛的同情,有这种意识,有超越国家、超越有限生活,去寻求永恒的意味愿望在里面。我就觉得中国当代作家,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欠缺的。那么鲁迅我觉得他是中国少有、对人生活做出决绝批判的作家,所以我们看到鲁迅是非常悲观的,为什么。他看到人世生活的有限性,看到人性上的有限性,看到了这些东西。但是,鲁迅依然没有完成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超越,他晚年写到过他,我觉得鲁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人的生活是无望的、人的生活是阴暗的,但在另外一条线还有一个阳光的东西在那里,作家可以揭示出来,鲁迅意识到了,但是生命没有给他时间。我觉得在中国的诗人当中穆旦、海子是比较少有的有超越意识的作家,这也是诸多读者读《沙床》时误解我的原因。我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所以我们很难理解那种超越性的追求。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追求以灵魂给人安慰这样的精神世界,我追求的是这样一个东西,无神论者认为这个是虚伪的,有神论者认为这个还不够。中国作家在这个一维度里探索还不够,整体是不够的。
葛红兵:还是最开始的话,我希望能够呼吁大家重视农村教育的问题、重视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配置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社会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在同一个城市里面,比如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城里面的小学跟乡下的小学是不是可以搞更多教师之间的互相交流。比如说结对性的教师之间互派,通过这种方法不仅仅在硬件方面帮助乡下小学提高,也在软件上帮助乡下小学提高。这个可以给我们孩子以更多的出路。我觉得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此负有更多的责任,应该站出来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呼吁。我觉得许多的人都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就像钱钟书说的那样,躲起来像鸵鸟一样,对呼吁那些人觉得他们是作秀、无聊,我觉得对这种事情我感到非常伤感。如果所有人都不来说这个事情,那么谁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社会整体性对这个不平等的麻木、视而不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我想谈教育观念整体上的突破。我觉得我们功利教育太多,非功利人道主义的教育、人类意识的教育、地球意识的教育太少。 最后我们教育观念要回到对孩子个性的尊重、个性的培养,培养千差万别的孩子,不是把孩子造成统一的一个模式,往模式里套,也希望这个社会的教育观念有一些变化。最后我想孩子们。实际上我一直在教育的领域里工作,关于911那次的现场社会调查给我的打击非常沉重,我一点都没有夸张这个说法。他也使我开始把我自己的重心也慢慢转移到这里面。以前中学请我演讲我是拒绝的,大学请我演讲我也拒绝,后来所有中学邀请我都接受,大学我也大部分都是接受的,还出了一本演讲集。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这个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如果我们孩子有欠缺,这是知识分子的欠缺,他们没有把孩子教好,我希望大家都应该来做这个事情。
参考资料:http://www.baleyuan.com/share/jiaoyuguan/jiaoyuguan06.htm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21-04-19
新课程理论中教育观主要包括的三观:学生观、教师观和教学观。
1.学生观主要包括的内容有:(1)学生是发展的人:第一,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第二,学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第三,学生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2)学生是独特的人:第一,学生是完整的人。第二,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第三,学生与成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3)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第一,每个学生都是独立于教师的头脑之外,不依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第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第三,学生是责权的主体。
2.新课改下的教师观主要包含的内容有:(1)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2)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3)从教学与课程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4)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来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社区型的开放教师。
3.新课改下的教学观主要包含的内容有:(1)教学从“教育者为中心”转向“学习者为中心”;(2)教学从“教会学生知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3)教学从“重结论轻过程”转向“重结论的同时更重过程”;(4)教学从“关注学科”转向“关注人”
1.学生观主要包括的内容有:(1)学生是发展的人:第一,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有规律的。第二,学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第三,学生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2)学生是独特的人:第一,学生是完整的人。第二,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第三,学生与成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3)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第一,每个学生都是独立于教师的头脑之外,不依教师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第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第三,学生是责权的主体。
2.新课改下的教师观主要包含的内容有:(1)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2)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3)从教学与课程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4)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来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社区型的开放教师。
3.新课改下的教学观主要包含的内容有:(1)教学从“教育者为中心”转向“学习者为中心”;(2)教学从“教会学生知识”转向“教会学生学习”;(3)教学从“重结论轻过程”转向“重结论的同时更重过程”;(4)教学从“关注学科”转向“关注人”
相似回答